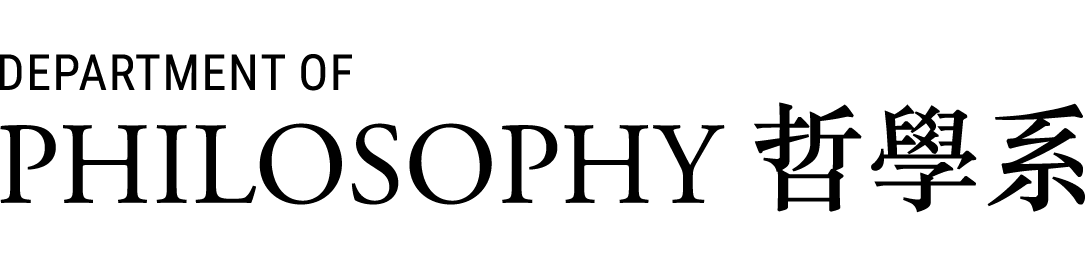賀倫斯坦教授
瑞士聯邦科技學院
榮休教授
賀倫斯坦教授一九三七年生於瑞士,曾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修讀哲學、心理學和語言學,一九七零年以研究現象學與前語言經驗的 論文在魯汶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賀氏曾任蘇黎世大學哲學系講師(一九七三至七四),亦曾於魯汶大學胡塞爾檔案館(一九七一至七三)、哈佛大學(一九七三至七 四)、夏威夷大學(一九七四)和科隆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一九七五至七七)任研究員。一九七六年,賀氏憑早一年出版的專書《雅各布遜的現象學結構主義》在蘇 黎世大學取得教授資格。從一九七七至一九九零年,賀倫斯坦教授任教於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哲學系,並於由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二年出任蘇黎世瑞士聯邦科技學院人 文學系哲學正教授。賀氏於二零零二年起為瑞士聯邦科技學院榮休教授。
賀倫斯坦教授為斐聲國際的學者,曾任史丹福大學語言學系(一九八一至八二)及東京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三至八四)訪問學人、東京大學訪問教授(一九八六至八七),以及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學院從事訪問研究(一九九六至九七)。
賀倫斯坦教授曾為雅各布遜及胡塞爾著作的主編(共四卷),並曾出版專論十部,包括《聯想的現象學》(1972)、《雅各布遜的現象學結構主義》 (1975)、《語言學—符號學—詮釋學》(1976),《論語言的可回溯性》(1980)、《人的自身理解》(1985)、《語言的共相》 (1985)、《從文化哲學的觀點看》(1998)、《蘇格拉底》(2002)以及《哲學地圖:思想的地點與路徑》(2004)。後一著作被譽為開啟了一 種嶄新的哲學撰作類型。賀氏亦曾發表超過八十篇論文。他的著作涵蓋範圍甚廣,包括現象學、語言哲學、詩學、文化哲學、跨文化理解的哲學、及地理哲學,並已 被譯成英、法、意、葡、俄、匈、中、日等多種語文。
賀倫斯坦教授自二零零二年退休後居於日本橫濱,但仍著述不斷。他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哲學心理學(身心問題,經驗、語言與思想的關係,人工智能與自然智能的比較)和文化哲學(不同文化間的不變項、文化內部的變遷,地理在哲學史和科學史中的角色)的各種課題。
賀倫斯坦教授為本系第三位唐君毅訪問教授,他將作出題為<蘇格拉底──回顧歐洲、展望亞洲>的公開演講,為本系主持一個為期四週的研究院研討班<地理的哲 學──哲學的地理>,以及在本系的教職員研討會中發表題為<自然倫理──倫理學中合法的自然主義>的論文。賀氏過去曾三度訪問中文大學。他於一九九七年首 訪中大哲學系,並於二零零零年出任本校新亞書院明裕訪問學人,然後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三訪中大,於本系及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合辦的第一屆東亞現象學國 際學術會議上擔任主題講者之一。
文章下載
本網頁內所有文章皆受版權保護,只供學術研究之用。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Humanity: the Conception of Hegel (up to 1831), of Jaspers(1949) and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ion (1999)” (PDF)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Die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hre Konzeption bei Hegel (bis 1831), bei Jaspers (1949) und heute (1999)”, in: Karl Jaspers –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hg. von Reiner Wiehl & Dominic Kaegi, Heidelberg: C.Winter, 1999, 163-184.
“Life like a Dream – Overdetermined Freud’s Timeliness for a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 (PDF)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Das Leben wie ein Traum – ueberdeterminiert: Freuds Vorbildlichkeit fuer eine Philosophie der Lebenswissenschaften”, in: Der Traum – 100 Jahre nach Freuds Traumdeutung, hg. von Brigitte Boothe, Zuerich: vdf (ETH), 2000, 139-157.
“A Dozen Rules of Thumb for Avoiding Inter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webpage)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in Elmar Holenstein, Kulturphilosophische Perspektiven. Schulbeispiel Schweiz – Europaeische Identitaet – Globale Verstaendigungsmoeglichkeiten. Frankfurt/M.: Suhrkamp, 1998, 288-312.
自歐洲回顧 ─ 在亞洲展望
蘇格拉底的形象過去曾具創意地和相應令人滿意地被解構;然而這一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再者,這些對蘇格拉底的舖陳方式──它們幾乎全數集中於他如何以堪作楷 模的方式把哲學、生命與死亡統一起來──已經退居為背景知識。今日的蘇格拉底研究,都聚焦於這位歐洲哲學先驅的理論革新。這次演講要處理的,是四個典型的 蘇格拉底式信條:
(1) 哲學是種助產術;
(2) 知識有情欲成分;
(3) 哲學是對自身的知識;
(4) 哲學持不可知論的態度。
(1) 一個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並不把自己視為導師,而是促成者。哲學家與人對話,令人們見識到所有人——不論女性或男性,亞洲人、非洲人還是歐洲人——都能夠從事哲學思考,即能夠反省和參與辯論。只要他們會說一種自然語言,就足夠證明他們有這種能力。
(2) 傑出的科學家們都不相信以單一原因就可以說明他們對知識的渴求。對權力和威望的追求,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充份的解釋。知識也有美感的一面,因而也有情欲的一面。與我們今日所認識的人工智能不同,人的自然智能包含著感情的向度。知識涵涉快樂。
(3) 黑格爾認為蘇格拉底體現了歷史上知識首次回指認知者自身。然而,在南亞,這個以對自身的知識為目標的轉向,早在蘇格拉底前的一至三個世紀就已出現。今日要 討論的是兩個有糾正作用的見解:沒有對他人的知識,對自身的知識是不可能的;而基於人的物理性自然的本性,若離開了對自然的知識,也不可能有對自身的知 識。相應而言,視蘇格拉底為把哲學研究從自然轉向人的心靈的看法,必須重新檢討。
(4) 哲學不單只檢視人們自以為知道某些事情時所持的理由,它也一直關注這知識的界限。我們對這界限的態度是個重要問題。持不可知論而沾沾自喜並不是有益的啟導原則。
不久之前的二零零二年,是距蘇格拉底被判服毒自殺的整整二千四百周年。這是探討他對死亡和死刑的見解的時機。據柏拉圖記載,蘇格拉底認為人的生命並非來自 自己,因而不應該毀滅一己生命這一觀點,我們起碼可說是令人失望的。這是個教條式的答案。更令人驚訝的是蘇格拉底雖被判死刑,但我們卻找不到他對死刑的任 何批判性評說。這與比他早一個世紀的孔子成強烈對比。然而,時至今日,希臘已廢除了死刑,中國卻還沒有。
地理的哲學和哲學的地理
History plays an important and well-known role in philosophy all over the globe, in East Asia as much as in Europe. Geography, its spatial counterpart, however, is much neglected, despite the obvious fact that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largely hinge on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from Plato and Aristotle to Montesquieu and Herder, the main geographical factors that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explain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terrain (soil) and climate. But at least as important is the environment in the literal sense or spatial connection. Why did philosophy in Europe start in Greece and not in Germany? The answer is simple: Greece, not Germany, lay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of the most advanced early urban and proto-scientific civilizations, those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from Egypt to Mesopotamia.
A transfer of ideas from one language or culture to another casts new light on them and stimulates other connotations. It so furthers almost automatically creativity.
It is a well known but insufficiently explained fact that accomplishments in philosophy, art, and science vary not only between the continents, but also with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China, and probably all countries.
Such observation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seminar on the basis of a newly published atlas of the glob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One of the goals will be a revised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atlas.
自然倫理: 倫理學中合法的自然主義
在倫理學中,「自然主義」是指這樣的見解:(1)我們可以由「是」(實然)推論出「應該」(應然),由「不是」推論出「不應該」;而且(2)一事物之為好的,是因為它帶來幸福、使人愉快、有用、促進生命、順應自然……等等。
(1) 對從實然推論出應然的反對意見最初是(隨著休謨)在現代歐洲出現,而這並非偶然。這些反對意見預設一套極端簡約的存在論,預設一切存在都是適然的, 而它們亦不是必然地如其所是。因此,先後出現的事物亦同樣是適然地按這個序列出現,而並非必然地如此。這些意見預設自然界並無目的。如果生物並不是為了追 求甚麼而生存,那麼這些生物的本性裏就沒有甚麼可以作為評價其行為的根據。
這個受到休謨質疑的推論,它的合法性在反面的例子裏——亦即由「不是」得出「不能」時——最為明顯。我們不能要求某人做一件他根本不能做到的事。在這裏問 題出現了:我們能否由「是」經過「能」而推論出「應該」?在進一步的自然主義的預設之下這是可能的:這預設就正如生物學家所講,在一種自然的能力與運用這 種能力的傾向——即「意欲」——之間是有著自然(無須外力)聯繫的。如果某人想得到些甚麼,他就應該做會幫助他達到這目標的事情。當然,這是預設了那目標
是比他達到它所需耗用的手段更有價值。
(2) 反對將道德上的「善」建基於幸福、快樂、效益、促進生命、與自然的和諧等等的意見,似乎是跟隨著一種對結構簡單的存在論的信念,或者最少是一種對簡單觀念 和思想的偏好,也似乎預設某種離開自然衝動的自足價值。對於這種想法我們可以反問:如果一樣事物不帶來幸福、快樂、功效、促進生命或者順應自然等等,它可 是在道德上是善的嗎?一個不帶來幸福、快樂、功效、促進生命或者順應自然等等的行為,會不會有一條普遍律則或者道德律令可以說明它?
在倫理學中,恰當的自然主義並不是將倫理上的善化約為「帶來幸福」、「令人快樂」、「促進生命」或者「順應自然」等自然謂詞的化約式自然主義,而是承認自 然性質為基本倫理性質的非化約式自然主義。這樣的自然主義將這些自然性質視為判斷道德行為時的必要條件,但就並非充份條件。善的概念與幸福的概念之間既有 些相似之處,但人們列出來作為他們幸福的條件那種種狀態,卻又不足以窮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