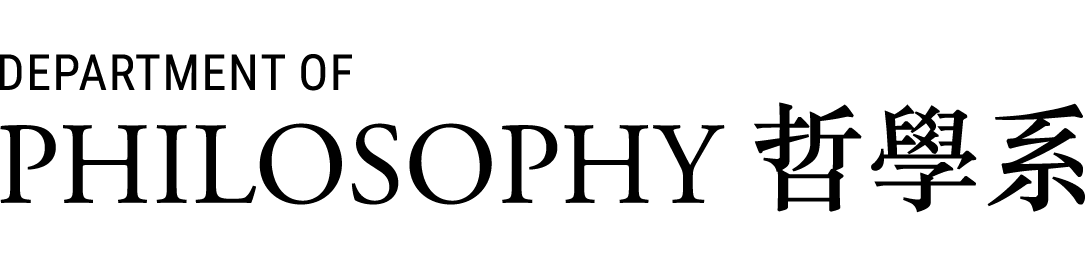陈嘉映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嘉映教授1952年生于上海,6岁到北京,读了六年小学、两年初中,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辍学,1968年到内蒙突泉插队,1976年初回北京。高考恢复后,考进北大西语系读德语,不久考研究生,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毕业后留校两年。1983年年底到美国,进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后在美国和欧洲几个文化机构工作。1993年回国,翌年回北京大学执教。2002年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系主任。2008年转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书至今。
陈教授以现象学研究尤其是海德格尔研究著称学术界,于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伦理与道德哲学、中国当代汉语哲学与思想等领域亦着力甚深。译有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1987初版)、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2001初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995初版)、《语言哲学》(2003初版)、《说理》(2011)、《何为良好生活》(2015)。 其他主要著作包括:《存在与时间读本》(1999初版)、《从感觉开始》(2005初版)、《无法还原的象》(2005初版)、《哲学 科学 常识》(2007)、《白鸥三十载》(2011)、《价值的理由》(2012)。其他主要译作有:戈尔(Al Gore)的《濒临失衡的地球》(1997初版;由陈嘉映主持并与他人合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2001初版)、万德勒(Zeno Vendler)的《哲学中的语言学》(2002初版);主编并参与翻译的作品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西方大观念》(2008)、《维特根斯坦读本》(2010初版)、J. L. 奥斯汀(J. L. Austin)的《感觉与可感物》(2010)、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伦理学,哲学的限度》(即将出版)。
Happiness and Uttermost Happiness

初看,“快乐”这个词的用法实在混乱:俗人沉溺于声色犬马,乐;壮士攀登希夏邦马峰,也乐;得志小人为轩冕而乐,恶徒甚至从施虐求乐;孔颜乐道,还是乐。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是,“快乐”并不是目的。我因为口渴去找水喝,即使焦渴得饮清泉带来快乐,我也不是“为了”快乐去喝水。的确,有些活动所追求的是快乐本身,就在“找乐子”,如嗑药、买春、溺乐;但并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活动,而否认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在做事,而不是在找乐子。
我们的确可以说,快乐本身是好的,但这不是说找乐子这样的事情是好的。这个“本身”说的是快乐处在它“本然的位置”之中——由向上的活动所引发,融合在上扬的情势之中。施虐的快感把快乐从它本来的上扬趣向抽离出来,扭结到堕落的活动之上,乃至若把“快乐”这个词用到施虐者身上,我们忍不住在其前加上“邪恶”、“变态”之类的形容词。
与之对照,有德之人的快乐则完全来自所行之事的上升。从善是向上的,古人说“从善如登”;德行系于生长,古人说“生生大德”。因行有德之事而获大乐是纯粹的快乐,不是因为它无涉痛苦,倒在于无论多少艰难困苦,只要生命在生长,有德之人就乐为之。这里的“快乐”是万物生生的自得之乐。在他生存的根底上通于生生之大乐,是为“至乐”。
共相与会通

我从汉斯•昆的〈真正的宗教〉一文入手来谈谈共相与会通。
当代基督教哲学家汉斯•昆不再认为基督教是普遍的宗教,基督教的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基督教是获得拯救的惟一途径。这是开明的态度,但带来一个疑问:“如果在教会和基督教之外已经存在着拯救,那教会和基督教还有什么必要存在?”
汉斯•昆依三层标准来回答这个疑难。这三层标准是以普遍性的程度来区分的,而普遍性又是在“共同点”或“共相”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一层 是基于人性的伦理标准。这一回答远不让人满意。核心疑问是:如果我们归根到底需要遵从存在着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人性伦理标准,我何不直接依这些标准行事, 却要假道基督教或其他任何特殊的标准?
我的基本思路是:不断向更普遍的共相上升无助于解决汉斯•昆面临的问题。一个人在其上获得其基本存在认同的层面,中国人、基督教徒、共产党员,原则上是历史—社会造就的层面。他要与不同身份认同的人之间进行交流,靠的不是放弃自己的既有身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而是通过平行的会通,在自身身份中找到能够接纳异质内容的渠道,就像用母语翻译别种语言一样。会通并不依赖于各种殊相之上的普遍者,会通依赖于殊相之间的翻译。即使说到救赎,人也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救赎。有人由基督教的上帝得到救赎,有人由华夏文明得到救赎。 有谁竟由普世宗教或普适伦理救赎,那仍然是一种特定的救赎,而不是更高的救赎。